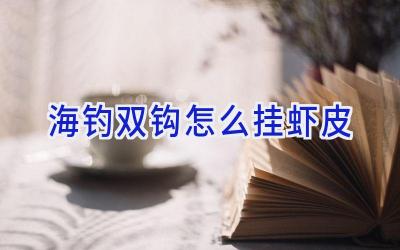清晨那口带着咸味的东北风,刮在脸上,总能把我从半梦半醒的混沌里拽出来。尤其是在船舷边,看着远处海面那层薄雾被旭日一点点撕开,露出波光粼粼的模样,心里头就只剩下俩字:踏实。这辈子跟海打交道,算起来也小四十年了,从愣头青一个,到如今偶尔也被人喊声“老李头”,手上这杆子、这线组、这饵,就像身体的一部分。
很多人问我,老李啊,你那么多年海钓,花样玩得不少,路亚、铁板、筏钓,我也都玩过,可为啥到了真格的,尤其是在近海礁区,你总爱倒腾你那对儿老掉牙的双钩?还非得是挂虾皮?嘿,这事儿啊,说来话长,但也简单。
要说这双钩,它不是什么高科技,就是两枚钩子串在同一条子线上,中间隔个十几二十厘米的距离,通常上方再加一枚活动铅坠。这套东西,看似笨拙,可要我讲,它就是这片海域最稳妥、最有效率的活儿。尤其是在那些水深五到十五米,底部有暗礁、有沙底、有海草交错的地方,那是黑鲷、黄鱼、鲈鱼、甚至一些小石斑的乐园。这些家伙,尤其是黑鲷,机警得很,有时候它不直接吞食,而是啄、是试探。单钩,你可能只感觉到轻微的蹭线,错失了机会;双钩呢?哪怕它只是轻轻啄了一下上面那枚钩子上的虾肉,下面那枚也可能因为你的轻微提拉,就意外地蹭到了它的嘴角,或者让它放松警惕,一口把整条饵线吸进去。一饵双吃,或者说,多一次中鱼的机会,这效率,谁能不爱?
我用这套东西,首先选钩子,那是有讲究的。我几乎离不开千又钩,尤其是千又3号到5号。这钩子,钩条够粗,抗拉力足,钩尖内弯,刺鱼稳、跑鱼少,而且钩门宽,挂虾皮那叫一个方便。如果水下障碍多,可能会选钩门稍微内收一点的丸世,少挂底。我把主线(通常是1.5号PE线,配上3号碳线前导,长度大概两到三米,主要为了耐磨和隐蔽性)下来,直接连接一个天平或者一个三向转环。这样能保证子线不易缠绕主线。然后,从天平或转环的两端,分别引出两根2.5号碳线的子线,长度我习惯一长一短,比如上面那根三十厘米,下面那根四十到五十厘米。为什么一长一短?这学问大了去了。潮水涌动起来,两枚饵在水下呈现的姿态就不一样,长的晃得更远,短的更稳定,给鱼更多选择,也更能模拟自然状态下饵料的飘动。
子线的选择,碳线那是必须的。它的比重比水大,能更快地将饵送到钓层,而且透明度高,在水下几乎隐形,不让警惕的鱼发现异样。更重要的是,它的耐磨性,在礁石区,这是你的生命线。
至于这虾皮,可不是随便找点虾肉就行的。我通常用的是新鲜的南极虾,或者基围虾切段。虾肉要取透明有弹性的部分,韧性好的,切成小指甲盖大小的方丁,或者直接用虾仁去头去壳。如果用整虾,那更是讲究。挂虾皮,我的原则是:宁可多穿,不可少穿;宁可隐藏钩尖,不可暴露钩尖。
看,这才是真功夫。
| 钩子型号 | 适配虾皮大小 | 目标鱼种偏好 | 钩门特点 | 挂饵要点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千又3-5号 | 虾仁、虾肉丁 | 黑鲷、鲈鱼、黄鱼 | 钩门宽,钩尖内弯 | 从虾肉一头穿入,埋钩尖,露出钩柄 |
| 丸世15-18号 | 整虾、大虾仁 | 黄鱼、小型石斑 | 钩柄短,钩尖内弯 | 从虾尾部穿入,穿透虾身,或L型挂法 |
| 管付12-14号 | 大块虾肉、虾头 | 真鲷、鳕鱼 | 钩柄长,绑线更牢固 | 从虾头部分穿透,虾肉平铺钩身 |
我是这么操作的:取一块新鲜的虾仁,用钩尖从它切面的一端轻轻扎入,然后顺着虾肉的纤维,像穿针引线一样,把虾肉一点点地往钩柄方向推。重点是,钩尖一定要藏在虾肉里面,不能露出来。为什么?你以为鱼是傻子?尤其像黑鲷,它那眼神,比鹰还毒。看到钩尖,它能立马掉头走人。我喜欢把虾肉在钩上穿成一个紧实的小团,或者让它自然地垂挂着,但确保钩尖被完美隐藏。如果用的是整只小虾,我会从虾尾部位的关节处,将钩尖穿入,然后顺着虾身,一直穿到虾头,最后让钩尖从虾眼或虾头附近露出来。这样,虾子在水下依然能保持比较自然的姿态,而且不容易被小鱼啃掉。
抛投,这又是一门学问。不是你扔得远就行的。要读懂潮水,这片海域,涨潮时水往哪个方向流,落潮时又往哪个方向走,心里得有数。我一般会根据船的位置和潮水的方向,选择一个上游或者侧上游的角度抛投,让铅坠带着饵料顺着水流慢慢下沉、漂移,而不是死沉到底。这样,饵料的动态才最自然,才最能引诱那些藏在礁石缝里的家伙。我的船钓竿,通常是2.4米到2.7米的软尾筏竿,调性不能太硬,二八调或三七调最合适。这种竿子,竿稍敏感,能清晰地传递水下的任何一点信息,哪怕是鱼儿轻轻地啄食,你都能感觉到那细微的颤动。我的纺车轮一般是3000型到4000型,速比不用太高,能稳稳地收线就好,刹车力要够用,Shimano Sedon或者Daiwa Legalis LT这种中端轮子就足够了,关键是手感顺滑。
控线,是这套钓法的灵魂。铅坠到底之后,不能让线死死地绷着。要留点虚线,让饵在水底随着水流轻微地跳动,模拟虾子在底部觅食或者躲藏的样子。手要时刻握着竿子,食指轻搭在主线上,感受那微妙的变化。有时候,中鱼不是那种猛烈的顿口,它可能只是一个轻轻的“笃”一下,然后线组瞬间变松了一点点,或者突然绷紧,像有东西轻轻拽了一下。这都是鱼在试探。这时候,你不能急着扬竿,要等。等它再来一口,或者感觉到竿稍一个明显的下弯,甚至伴随着“嗡”的一声传导到手中,那就是它把饵吞进去了!
扬竿,要快,要有力,但不能是那种蛮力。我喜欢用一个低位扫竿的动作,从身体前方,快速向上向后扫出,让钩尖瞬间刺入鱼嘴。记住,刺鱼要果断,不能犹豫,否则它可能把饵吐出来。
中了鱼,搏鱼的过程更是考验。黑鲷这东西,劲儿大得很,而且喜欢往礁石缝里钻。中鱼的第一时间,就要把竿子高高地扬起,把鱼头带离水底,不要给它钻礁石的机会。轮子的泄力要调整得恰到好处,不能太紧,也不能太松。太紧了容易断线,太松了鱼跑得欢。那吱吱作响的泄力声,是渔获的前奏,也是你与鱼之间力量的对话。要利用竿子的腰力,一点点地消耗鱼的体力,让它打圈圈,而不是一味地往外冲。这种感觉,那种竿尖传递回来的搏动,每一寸弯曲的弧度都充满了力量感,你甚至能感觉到鱼尾的每一次摆动,那才是真正的享受。
我记得有一年冬天,海上风浪不大,但水冷得刺骨。我带着我那套老旧的双钩和虾皮,在烟台的养马岛外礁,找了个背风的深水湾。那天大部分钓友都空军,路亚的,筏钓的,都抱怨鱼不开口。我耐着性子,一点点地拖钓,用最慢的速度,让虾皮在水底轻轻蹭着。突然,竿稍猛地一个大弯弓,差点把杆子从我手里拽飞出去! 那种力量,绝对不是小鱼!我当时就想,这肯定是条大货。我稳住心神,和它周旋了将近十分钟,那鱼就跟个小钢炮似的,几次都差点把线拉断。最终,在冰冷的海水里,我拉上来一条足足有七斤多的野生大鲈鱼!那鱼出水时银光闪闪的鳞片,在冬日阳光下,简直像个艺术品。当时,周围的钓友都惊呆了,跑过来问我用的什么饵,我指了指桶里的虾皮,他们脸上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等待都值了。
有人说,现在钓鱼都是玩装备,玩科技。没错,好的装备能帮你省不少力气,提高效率。但我总觉得,钓鱼最根本的,还是对大海的理解,对鱼情的判断,以及那一颗不浮躁、不放弃的心。钓鱼,其实就像人生,有时候你拼命去追,却一无所获;有时候你耐心等待,反而能收获意外之喜。这双钩和虾皮,它简单,它纯粹,它没有那么多花哨,但它能让你真正感受到海的呼吸,鱼的脉搏。它提醒我,最原始的,往往也是最有效的。
现在回想起来,那海风吹拂脸庞的咸湿感,那海浪拍打礁石的轰鸣,那鱼儿出水时扑腾的生命力,甚至那虾皮淡淡的腥味,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这不单单是钓鱼,它更是我与大海之间,一场永不结束的对话。而那对双钩,就是我连接这片深蓝色世界,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纽带。